新就业形态:从高效到长效

导语
新就业形态的本质是基于互联网平台开展的零工经济。在数据算法等机制作用下新就业形态得到高效发展;而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需要以劳动者为中心构建社会保障和权益保护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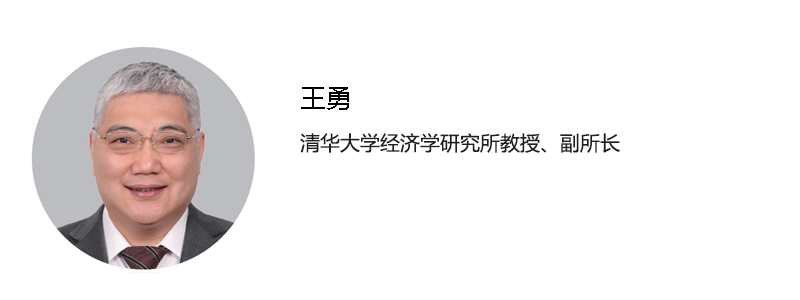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不仅关系个人发展和家庭幸福,更是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最重要的微观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必须抓紧抓实抓好。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多种举措来缓解就业压力,包括国有经济部门扩大招聘规模、保护和支持中小企业、开展就业培训等。但笔者认为,更需借助互联网平台的力量,推动灵活就业、零工经济等新就业形态的发展。
零工不零:新就业形态渐成主流
所谓灵活就业,是指采取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性和弹性工作时间等多种灵活的就业方式。从事灵活就业的人群往往被称为“零工”,因此灵活就业也被称为零工经济(Gig Economy)。国际劳工组织曾把其称为“非正规部门就业”,原因是灵活就业者所就业的部门往往是微型企业、家庭企业和独立服务者三类,工作时间长短不定,就业收入不稳定,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且在多数情况下官方统计部门也无法统计。因此,传统上,灵活就业并不被视为就业的主要渠道,只是正规就业部门的补充,零工经济并没有引起各国的重视。
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依托各类互联网平台,特别是服务类平台,可以对零工和雇主进行高效撮合与匹配,使得零工经济有了巨大变化。零工人群搜寻和获得工作的机会变得更加容易,使得就业时间达到甚至超过正规部门,相应地,也产生了较为稳定的就业收入。以至于“零工不零”,逐渐成为一种新型就业形态。与传统就业形态相比,其具有就业门槛低、创业成本小,可满足个性需求,增加市场经济活动总量等优势[1]。因我国平台经济发展较快,所以这种新就业形态发展也较为迅猛,并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达到了约2亿人[2],其中依托互联网平台开展新就业形态的人数超过8400万人,而为新就业形态提供服务的平台企业所雇佣的员工也有631万人,二者合计超过了9000万人,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中,灵活用工人数占比已经超过1/4(25.6%),正在逐步成为主流的用工方式[3]。
对于这一趋势,我国政府因势利导,陆续出台了支持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的政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新就业形态”的概念,指出要“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力度”。2018年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运用“互联网+”发展新就业形态。同年9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发改委)等19个部门出台了《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动数字产业发展壮大,拓展就业空间,培育更多新就业形态,吸纳更多就业。此后,2020—2021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六稳六保”的首要任务是“稳就业保就业”,发改委以及人力资源部等相关部委多次出台鼓励多渠道灵活就业推动新就业形态发展的具体指导意见。2022年10月,更是首次把新就业形态写进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
如何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一决议?特别是如何更好地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实际上,只有深入理解新就业形态特征及其在我国的发展情况,特别是互联网平台对新就业形态的支撑作用机制,明晰其优势和短板,才能出台更加科学的扶植性政策和必要的规范性措施与监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新就业形态是指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特别是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种就业新模式,体现为劳动关系灵活化、工作内容多样化、工作方式弹性化、工作安排去组织化、创业机会互联网化,正在成为吸纳就业的一条重要渠道[4]。
基于此,笔者认为,新就业形态的本质是依托互联网平台开展的零工经济。根据依托的互联网平台的类型,新就业形态具体类型包括:①依托本地生活服务类平台提供个体劳动服务的就业形态,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闪送骑手、家政保洁人员、教学辅导等;②依托电子商务等商品交易类平台进行个体经商人员,或者为平台商户提供网页设计、广告模特、带货促销等商业服务人员;③依托用户生产内容平台(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 进行多种形式内容创作的人员,如文学创作、影视剪辑、经验分享、观念写作等人员;④依托专业任务众包平台(Crowdsourcing Platform)提供专业服务的就业形式,如数据标注、字幕翻译、在线咨询、摄影指导等。这些新就业形态也创造了众多新型岗位名称。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首次标注了数字职业(代码为S),共标注数字职业97个,占职业总数的6%,除上述提到的网约车司机等岗位名称外,还包括城市管理网格员、互联网营销师、信息安全测试员、区块链应用操作员、在线学习服务师等技术密集型职业。
上述新型就业形态为就业者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以至于多数就业人员愿意长期选择这一就业方式。根据美团发布的调查报告,2020年新形态就业者中月收入不到3000元的仅占14.3%;收入在6001~12000元的占比为35.7%,超过12000元的占比超过21.2%,二者合计超过56.9%。说明绝大多数新形态就业人员都有着较为稳定的收入水平。并且有71.6%的从业者愿意从事至少两年以上该工作,仅有7.9%的从业者不看好新就业形态,但其中愿意回归传统职业的却仅为3.7%。
此外,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农业生产”“互联网+乡村旅游”等方式催生创意农业、分享农业、众筹农业、农村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帮助农村人口参与新型就业形态,并为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动能,为农村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注入活力。截至2022年6月,累计1120万人返乡回乡创新创业,平均每个主体带动6~7人稳定就业、15~20人灵活就业[5]。
高效:数据和算法机制

图源:VEER
与传统劳动力市场相比,互联网平台对零工经济的支撑作用机制是基于数据算法的匹配撮合机制,极大降低了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搜寻成本等市场摩擦,提高了零工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
首先是由于有关劳动者的能力和品行等信息不对称,即所谓的“人不可貌相”,导致的潜在雇主无法了解求职者能力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如果雇主采用按照劳动力的平均能力水平来支付工资的话,则高能力的劳动者将不愿接受此工作,而低能力者则愿意接受,形成了千里马反倒被淘汰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的不利结果。
根据2001年诺贝尔奖得主斯宾塞(Spence,1976)的研究,对于高能力者来说,避免这一不利结果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接受难度较高的高等教育并获得学位文凭,以此来主动传递高能力信号[6]。这一理论对于传统劳动力市场中各种文凭证书的作用做了非常重要的理论解释,同时也说明,对于很多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求职者来说,其在劳动力市场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即使拥有较高的能力也未必能获得理想的就业岗位和机会。
其次是在使用劳动力的过程中,劳动者的努力程度往往无法被直接观察到,或其付出和产出之间往往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导致间接测度也较为困难的问题。在这种努力难以监督的情况下,劳动者会采取被称为“道德风险”(Moral Hanzard)的机会主义行为,即懈怠和偷懒,从而会损害雇主的利益。雇主此时往往会采用效率工资(Efficiency-wages Theory)的激励机制——付给劳动者高于市场均衡的工资水平。在这种激励机制下,如果劳动者偷懒,一旦被抓住并解雇后,其新找的工作的工资水平往往是市场均衡工资,低于效率工资,因此劳动者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偷懒并努力保住当前工作。效率工资尽管可以起到激励作用,但由于高过市场均衡工资,会使得企业减少雇佣员工的数量,甚至在遇到经济下滑时,往往不会选择降薪,而是选择裁员,进一步减少了就业岗位。此外,一些企业在规模做大以后,往往会滋生官僚文化,考察员工是否努力往往单纯依赖工作时长,如是否早来晚走等,这打击了一些富有创意和高能力但自由懒散员工的积极性,他们往往也会主动或被动离开职场。
最后是求职者与岗位匹配所产生的搜寻成本问题。求职者希望找到适合自己且薪水满意的工作,雇主希望雇用能够胜任特定岗位任务的员工,为提高匹配程度,双方都会在劳动市场中进行搜寻。搜寻会产生成本,这一成本不仅是双方在搜寻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还包括间接成本,即企业岗位空缺所产生的效益损失,求职者待业所产生的收入损失。根据2010年诺贝尔奖得主戴蒙德(Diamond,1987)的研究,搜寻成本的存在导致劳动力市场因无法匹配难以出清,即一方面企业存在岗位空缺;另一方面却存在很多工人失业的现象[7]。
上述提到的劳动力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搜寻成本三大摩擦性因素在零工市场产生的后果更为严重。零工市场的求职者大部分缺乏高等教育的文凭证书,无法有效传递其能力信息;因零工雇佣关系持续时间短,效率工资在零工市场几乎不会发生作用;零工市场中雇主的岗位往往是临时或季节性的,搜寻成本和匹配难度更高,导致匹配性失业严重。正是因为零工市场中没有找到合适的机制解决上述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市场摩擦问题,导致其没有办法成为主要的就业渠道。
但互联网平台凭借其连接功能和数据优势,使得上述三类摩擦性问题得到了较大的缓解。
互联网广泛的连接功能,汇聚零工需求和供给,可以有效降低搜寻成本。根据2014年诺贝尔奖得主让·梯若尔与其合作者(Rochet et al.,2006)的研究,平台企业通过搭建网络平台,连接各类用户,形成多边市场,促进两类或者多类用户通过平台互动,达成交易[8]。平台经济这一连接功能将人与商品、服务、信息、娱乐、资金等直接连接起来,由此使得平台具有交易、社交、娱乐、资讯、融资、计算等各种功能,极大地提高了市场运行效率。就劳动力市场来说,这种连接功能将各种临时性的雇主需求汇聚在一起,将各种具有能力和时间空闲的就业者汇聚在同一个平台上面,并借助快捷和灵敏的在线搜集机制,使得求职者和空缺岗位得到高效率的匹配,极大地降低了搜寻成本,进而提高了新形态就业水平。
例如,网络销售类平台和生活服务类平台直接将平台内部的买家、卖家,以及提供支付、运输等商业服务的第三方连接起来,极大地降低了他们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云账户发挥数字技术优势,高效连接供需两端,对接生活管家、视频创作者等28种职业类型人群,就业范围覆盖视频传媒、分享社区、本地生活等15大行业60余个细分领域;阿里巴巴的“云客服”技能可以通过简单的在线培训轻易获取,极大地降低了这一岗位对于前期人力资本投入的要求,同时也解决了大量具有身体缺陷或行动障碍人群的就业需求;近年来兴起的“村播”,通过互联网平台直接对接农户与消费者,在为农户提供收入获取机会、提高收入的同时,也推动了农产品供应链的升级。
互联网平台可以依据海量数据,开发甄别算法,并建立在线声誉机制,降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平台企业依托平台用户以及零工的个人信息和使用习惯等大数据,开发智能甄别和匹配算法,对劳动者进行任务分配、任务监督、任务反馈等,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平台利润。比如,平台会通过“算法技术”对工作路径策略进行排列组合,从而计算出劳动者高效率、短时间的工作形态,形成“算法优化”“算法监督”等(李营辉,2022)[9],改善了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
例如,网约车平台可以根据网约车所处地理位置进行实时派单,并可以确切了解每一个司机每天的拉单量、行车违章情况、驾驶平稳程度等情况,还可以监控对乘客的服务质量——是否绕路、语言是否有礼貌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出租车行业的服务水平,提升了用户需求,进而增加了行业的就业数量。
此外,所有的零工服务平台都建立了用户的在线反馈和评价机制。比如,在家政用工平台上,除收录每一位家政人员的介绍信息,还会呈现该家政人员的接单量以及雇主的满意度评价,这些评价信息为潜在雇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决策参考,他们往往愿意出高价选择评价较高的家政人员。这一评价体系激励了家政人员的敬业精神,缓解了其道德风险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使这一市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长效:保障与保护
正是在互联网平台连接功能和算法功能的双重加持下,新就业形态的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平台企业依托这两种功能开展业务、创造营业收入,既解决了就业,又提高了收入。然而,在新就业形态衍生出一系列新运行机制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福利保障问题。
首先是新就业形态下零工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我国采取的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三位一体”的模式,即政府、企业和个体按照一定比例共同承担社会保障资金。然而,新就业形态多属灵活用工,难以符合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框架下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导致零工社会保障无法纳入上述“三位一体”模式。从平台方来看,零工和雇主都属于独立经济主体,平台仅仅为二者提供撮合交易服务,不应分担社保。从雇主方来看,由于零工并非雇主的正式员工,甚至部分企业利用平台进行“去劳动关系化”,以此规避法律规定的分担员工社保责任义务。从零工自身角度来看,其流动性高、收入不稳定、社保关系的区域转接手续烦琐等原因,导致他们的参保缴费意愿较低,普遍存在不缴或断缴现象。随着零工经济规模的扩大以及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社会保障问题将面临越来越突出的矛盾。
其次是新就业形态下平台算法与零工的劳动权益保护问题。在新就业形态中,很多劳动服务需求都属于即时需求(On-demand Service),需要互联网平台借助数据和算法机制进行实时派发。这些算法机制往往以效率为导向,通过收集零工服务数据,优化派单,压缩时间,以更好满足即时需求服务,甚至会基于订单完成的时间长短来确定奖惩机制。但这些算法往往不会考虑偶然性因素,忽略劳务场景有可能遇到的拥堵、故障、沟通等因素,造成零工受困在算法中。对于零工者而言,只有当平台上的排名越靠前时,被派单的可能性才越高。比如,在外卖行业,骑手的收入取决于接单量、准时率、差评率等,其中准时率是最重要的,如果超时,系统会自动扣提成,接单量再大也是徒劳。但平台上的算法则把配送时长一再压缩,如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单均配送时长已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为了保障准时,不少骑手只好超速、闯红灯甚至逆行,由此造成交通事故发生率不断上升[10]。牛津互联网研究院也发现,零工平台分派任务的算法会导致零工者持续过劳,与其他劳动者相比,零工者缺乏保障。
算法不仅有可能为提高效率而忽略了零工权益,也有可能借助算法不透明来损害零工的薪酬。零工的收入属于计件工资,平台从员工的计件工资中提成。尽管平台企业会明确提成比例,但这一比例往往还会受订单完成量、用户差评率等多个考核指标的影响,导致实际的提成比例并不透明。一些平台则利用这种模糊性来侵占零工应得的劳动收入。比如,纽约市曾在2019年规定了需要根据“派送接单率”(Utilization Rate)来计算网约车司机的薪酬,即要把接单时间和空载时间综合考虑在内,以避免平台企业侵占网约车司机的薪酬。
最后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问题。平台经济存在的注意力头部现象,导致同类群体内部收入差距很大。注意力头部现象是指平台企业或个人运用算法推荐获取流量资源或者利用眼球效应获取注意力等。获取流量资源越多,相应的注意力资源越多,由注意力经济带来的商业利益就会越多,进而导致同类劳动者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变得很大。比如,艾媒咨询监测数据发现,2020年中国网络主播平均月工资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占比为84.1%,其中收入在4500~8000元的主播占比为37.2%,而收入在5万以上的主播只占0.6%[11]。除了注意力分配因素外,性别歧视因素也使零工收入产生差异。根据Barzilay和Ben-David对某在线平台的研究,即使在研究人员控制了经验、职业类别和评价反馈分数之后,女性的时薪要求仍比男性低37%[12]。
改进:从高效到长效

图源:VEER
为使新就业形态逐步成为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就业“新渠道”,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制定或改进政策:
第一,针对零工缺乏有效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问题,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引导零工以个人身份或个体工商户身份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用和基本医疗保险费用。这两项基本保险费用也可以由平台企业或委托的第三方劳动服务平台企业为零工进行代付代缴。此外,平台企业还需要根据零工的工作场景需要,联合保险机构,制定合理的意外伤害险等工作险种,为零工提供充分的风险保障。
第二,明确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建立协同治理体系,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保障权益。结合不同类型平台特点,将主体责任与公共治理相结合,进行协同治理。在平台内部,强调平台企业私人治理作用,加强对雇主酬金发放监管,发挥其自身对劳动者权益保障组织与管理作用;在平台外部,政府落实公平就业制度、健全最低工资和支付保障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协同维护劳动者保障权益新格局。
第三,改进平台算法、合理分配流量,缩小平台内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收入差距。首先,规范平台算法推荐。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向劳动者提供工作调度服务的,应当保护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等合法权益,建立完善平台订单分配、报酬构成及支付、工作时间、奖惩制度等相关算法。其次,合理分配流量资源。在依靠行政命令让平台之间流量相互流通的基础上,遵循公平公正原则,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建立规范的流量结算体系,促进流量资源公平合理分布,进而缩小平台内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注释:
[1] 易定红. 疫情下我国就业形势与就业模式变化 [R].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2.
[2] 艾媒咨询. 2022 年中国灵活用工行业市场调研分析报告 [R]. 广东:艾媒咨询,2022.
[3]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R]. 北京:国家信息中心,2021.
[4]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 十四五”规划《纲要》名词解释之236|新就业形态[EB/OL]. (2021.12.24) [2023.1.9]. https://www.ndrc.gov.cn/fggz/fzzlgh/
gjfzgh/202112/t20211224_1309503.html?code=&state=123.
[5] 邓小刚.“ 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R]. 北京:中共中央宣传部,2022.
[6] Spence, Michael. Informational Aspects of Market Structure: An Introduction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6, 90(4):591-597.
[7] Diamond, Peter. Consumer Differences and Prices in a Search Model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7, 102(2):429-436.
[8] Rochet, Jean Charles, Jean Tirole. Two-Sided Markets: A Progress Report [J].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 37(3): 645-667.
[9] 李营辉. 被算法裹挟的“裸奔人”:新就业形态下网约工群体劳动权益调查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7):12-19+39.
[10] 赖祐萱.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EB/OL]. (2020.9.8) [2023.1.8]. https://mp.weixin.qq.com/s/Mes1RqIOdp48CMw4pXTwXw.
[11] 艾媒网. 2020 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收入情况及问题分析 [EB/OL].(2020.12.31) [2023.1.8]. http://yl.oneroadedu.com/source/article_show.
php?id=4167.
[12] Barzilay A R, Ben-David A. Platform Inequality: Gender in the Gig-Economy[J]. Seton Hall Law Review, 2017, 47(2): 393.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仅供读者参考,并不作为投资、会计、法律或税务等领域建议。编辑:潘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