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快转向全面鼓励生育的政策

导语
面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与“少子化”挑战,中国应尽快从限制生育向全面鼓励生育的政策转变,通过构建与生育相关的政策支持体系,充分发挥传统“家本位”文化鼓励生育的功能,利用多元化的福利配套政策,降低年轻一代的生育成本与养老负担,提高他们的生育意愿。从单纯放开生育的政策向宏观层面社会公共政策的发展,应成为鼓励生育政策的重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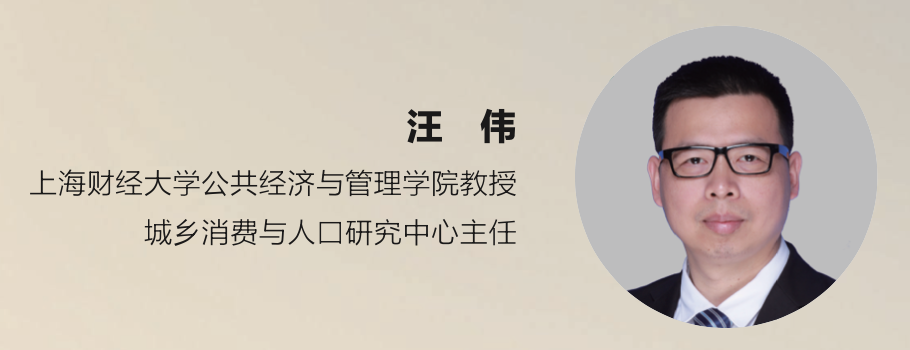
人口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的重大问题。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得益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和快速的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中国成就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并成功跻身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蔡昉,2010)。
近年来,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以上人口近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65岁以上人口约1.91亿人,占总人口的13.5%,相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别上升了5.44个和4.63个百分点。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于2010年达到最高点74.5%;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于2013年达到最高点(约10.06亿人),此后每年以超过300万人的速度减少,2020年下降到96776万人,累计下降了近4000万人。
低生育率趋势仍将持续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就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高达5.81,到90年代中后期,急剧下降至1.8左右(邬沧萍等,2003)。尽管中国政府近年来加快了生育政策调整的步伐,在2013年底和2015年底分别放开了单独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生育“二孩”,但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仍然没有逆转。到2020年,总和生育率进一步降至1.3,远不及2.1的生育更替水平。从新生婴儿的出生数量来看,只在政策放开的第一年略有上升,后续年份继续呈现下降的趋势,2020年的新生婴儿只有1200万,创下了自1961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国家统计局,2021)。以上数据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趋势日益明显。
Lutz和Skirbekk(2005)认为TFR降至1.5以下后,社会就会陷入“低生育率陷阱”,较长时期难以回升到正常世代更替水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经验表明,即使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依然难以逆转。2021年5月,中国全面放开了生育“三孩”,但可以预计,低生育率的趋势仍将持续。
从限制生育向全面鼓励生育的政策转变

如果说过去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逻辑主要是担心生育率过高带来的人口增长过快,经济社会发展容易掉入“马尔萨斯陷阱”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更应担心生育率过低和人口负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冲击,如劳动力数量急剧减少,经济增长率、劳动生产率与国际竞争力下降,养老负担日益沉重与公共财政压力上升等问题。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欧洲一些先后面临超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或地区都无一例外地遭遇过上述困境。
在一个低生育率的社会中,生育更多的孩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
其一,生育更多的孩子对修正失衡的人口年龄结构、增加未来劳动力数量、减缓老龄化的速度具有一定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降低家庭和社会的养老压力。
其二,新出生的人口能直接扩大家庭养育消费支出以及与政策相关的行业(如婴幼儿用品、家政等产品与服务)的消费需求,同时也有助于降低预防性养老储蓄。还有利于提升消费市场潜力,为扩大中国的消费需求带来新的契机(汪伟,2017)。
其三,从人力资本积累角度来看,家庭对新生子女进行教育投资,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扩大人力资本规模,也有助于提高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和潜在经济增长率。
关于计划生育是否仍然具有存在的必要性,众多的研究表明,近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王丰,2010;左学金,2010;沈可等,2012;汪伟,2017;蔡昉,2020)。从家庭的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来看,2017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显示,受访家庭意愿生育子女数的均值为1.88个,实际生育的数量只有1.42个,说明当前的生育政策在平均意义上对家庭并不构成实质性的约束,生育控制政策更多的是约束具有少数高生育意愿的家庭。因此,面对咄咄逼人的“老龄化”与“少子化”趋势,着眼于人口数量控制的传统计划生育政策思维需要进行根本性的转变,中国应尽早从过去的生育控制政策转向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的政策。
养老与抚幼的政策设计

毫无疑问,生育成本高昂与养老负担过重是年轻一代低生育的重要原因。因此,真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家庭生育意愿的对策,应该从各种有利于降低生养孩子成本与养老负担的公共政策中去寻找。
从国际经验来看,直接提供现金支持或进行税收减免是分担家庭生育成本并刺激家庭生育意愿的主要方式。比如,美国向家庭发放高额的生育津贴并根据家庭子女数量进行税收减免,俄罗斯设立专门的“母亲基金”来补贴家庭生育,法国根据不同家庭的生育子女数量和子女年龄的差异构建了育儿津贴体系等。中国可以借鉴上述国家的经验,加大对生育的财政支持力度,通过多样化的津贴设计来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和养育子女的成本。
结合当前的三孩生育政策,政府可以对多孩家庭采取梯度生育补贴,以此来提高家庭生育的意愿。另外,在发放津贴的同时,可以考虑辅之以税收优惠政策,比如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可以享有教育、医疗、住房等多方面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为不同生育意愿的家庭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激励和保障。
中国家庭的幼儿照料负担较重,大部分地区0~3岁的托育服务机构供给严重不足,照料子女的时间成本较高是生育政策放松后家庭生育积极性不高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国应建立更多的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并完善托幼服务体系,以满足放开生育政策之后,家庭日益增长的托育照料需求,缓解家庭的照料负担。在这方面,英国、瑞典等国的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它们通过设立社区儿童支持系统、为学龄前儿童提供免费的保育场所、完善儿童医疗服务体系等方式为家庭营造了良好的育儿环境,满足了家庭的托育照料需求,提高了家庭的生育意愿。
同时,考虑到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较高,生育之后难以在短时期内迅速返岗,这种来自“生育—工作”的冲突在给家庭带来经济压力时,也会影响育龄女性在就业市场上的表现与职业发展前景。因此,中国也应通过法律或制度设计来保障女性的就业权利,以缓解女性生育后的多重压力,比如可以借鉴并引入北欧国家早已推行的男性产假和“父亲的育儿假”等来完善现有的产假制度体系(沈可等,2012),同时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并出台为因生育中断就业的女性提供再就业的法律法规等。此外,中国也应对育龄女性员工较多的企业采取适当的税收优惠,减少企业对育龄女性的就业歧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可以促进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与家庭之间有效分担。
另外,应当注意到,在“高龄少子化”背景下,日益累积的长寿风险也会增加家庭的赡养负担,进而影响到年轻一代的生育决策。尤其是对于双方为独生子女的年轻夫妻而言,养老与抚幼压力的叠加会进一步降低他们的生育意愿。因此,中国鼓励生育的政策设计也应着眼于降低年轻一代的养老负担,加快推出“一老一小”相关配套政策,这样不仅可以缓解年轻一代的养老压力,也能减少他们生育子女的后顾之忧。
虽然中国家庭的生育意愿受到了生育成本和养老负担上升的冲击,但我们不能忽视中国传统“家本位”文化鼓励生育的功能。事实上,生育决策往往并不仅仅由家庭中承担生育责任的夫妻二人独立做出,受传统“家本位”文化的影响,家庭的生育决策还与父母的偏好和行为紧密相关。由于中国传统的“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以及基于亲子关系建立起来的纽带,父母通过提供经济帮助和隔代照料可以降低成年子女的生育成本,父母的支持行为可以看作是向子女传递生育意愿,这有利于提高子女的生育概率。
总之,面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与“少子化”挑战,中国应尽快从限制生育的政策向全面鼓励生育的政策转变,通过构建与生育相关的政策支持体系,充分发挥传统“家本位”文化鼓励生育的功能,利用多元化的福利配套政策,降低年轻一代的生育成本与养老负担,这样才有可能提高家庭的内在生育意愿。此外,中国还应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宏观层面政策去提高人口的质量。从单纯放开生育的政策向宏观层面社会公共政策的发展,应成为生育鼓励政策的重心。
参考文献:
[1] Lutz W., and Skirbekk V. Policies Addressing the Tempo Effect in Low-fertility Countries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5, 31(4):699-720.
[2] 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J]. 经济研究, 2010, 45(4):4-13.
[3] 蔡昉. 如何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 [J]. 国际经济评论,2020(2):4, 9-24.
[4] 国家统计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R]. 北京:国家统计局, 2021.
[5] 沈可,王丰,蔡泳. 国际人口政策转向对中国的启示 [J]. 国际经济评论,2012(1):6, 112-122.
[6] 汪伟. 人口老龄化、生育政策与中国经济增长 [J]. 社会科学文摘,2017(3):52-54.
[7] 汪伟. 如何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J]. 学术月刊, 2017,49(9):9-12.
[8] 王丰. 全球化环境中的世界人口与中国的选择 [J]. 国际经济评论,2010(6):5, 70-80.
[9] 邬沧萍,王琳,苗瑞凤. 从全球人口百年(1950~2050)审视我国人口国策的抉择 [J]. 人口研究,2003(4):6-12.
[10] 左学金. 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J]. 国际经济评论,2010(6):6,127-135.
*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应对策略研究(71773071)”、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人口老龄化对中国教育投资的影响研究(16PJC034)”的研究资助。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编辑:潘琦。